我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,也经过了非常痛苦的、探索的过程,刚开始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故事好写,好像所有的故事都被别人写了,当看到别人写了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故事,突然走红以后,我再来写知识分子的题材,马上就感觉这个题材已经过时了;当别人写一个在长江上放排的故事成功之后,我再来写又感觉到过时了,所以,当时是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去寻找能够写到小说的故事。
这样的寻找非常痛苦,结果也是很凄惨几乎找不到。
真正让我感觉到有东西可写了,是在1984年我到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。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是军队的院校办了一个文学系。在这两年之间我觉得没有学到多少东西,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每个人找到了自我,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。
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方向,过去我就感觉到,我们的小说还是写英雄人物、我们的小说还是要写这样的传奇经验、我们的小说还是应该写出惊天动地的事件。感动人,让人哭、让人怒、让人乐。
只有这样一些巨大的、庞大的题材才有可能写到小说里去,通过学习其他人的创作经验,通过听了很多作家的现身说法,通过大学文学教授们给我们讲述国外的很多成功作家的创作经验,我突然意识到,实际上写作就是应该从身边的琐事、小事写起,过去认为不能够写到小说里的很多细碎的,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事情经过文学的手段把它变成文学作品。
观念改变之后,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户,或者说如同在一道河上打开了几条久被封闭的闸门。过去认为不能变成小说的很多个人经验,突然感觉到变成了非常宝贵的小说素材。
我过去生活了几十年的村庄,过去认为毫无故事,现在感觉每一个家庭都存在着可以写到我小说里去的人物,而每个家庭的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都变成了很好的小说情节。
村庄的每一栋房屋、每一条胡同、村后河边上的每一棵树木,河床上每一座小的石桥,包括我们田野的每一块庄稼地,我们生产队饲养的每一头牛、每一头骡子、每一匹马都可以变成我小说里的素材。
我在农村生活的20多年,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,而且是无意累积的经验。一时间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我的作品。这样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,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就是文学观念的一种革命。
我的成名之作就是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。在座的很多朋友肯定已经看过。这篇小说实际上得力于一个梦境。
有一天早上,在军营宿舍,似醒非醒的状态下,看到了一片很广阔的萝卜地,一轮红日从东边冉冉升起。从萝卜地的中央突然站出来一个身穿红衣的、丰满的农村少女。她手里拿着一根鱼叉,然后从地下叉起一个红色的萝卜,她就高举着萝卜对着太阳走过去。
这个画面非常辉煌也很壮美。我醒了以后马上对我的几个同学说,我刚才做了一个梦,我要把它写到小说里去。就对他们讲述我刚才说的这个梦境。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变成小说呢?
但是有一个同学说,你先把它写出来我们看。我用了很短的时间,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初稿,在写的时候完全依靠梦境是不够的,就调动了自己少年时期的一段生活经历。
因为20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里面,类似的经验太多太多了。所以自己开始写,各种各样的、五花八门的小说都写出来了,像《爆炸》、《球状闪电》、《金发婴儿》等一批中短篇小说。
2 《红高粱》是一部自由的小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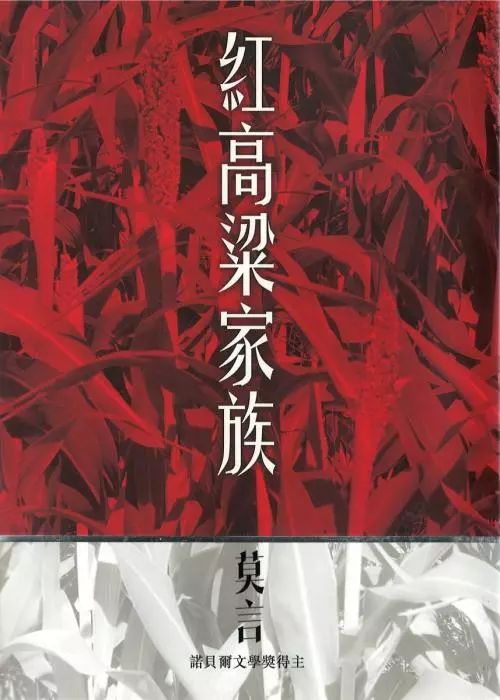
《红高粱》系列的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。
《红高粱》这部小说,我自己是把它作为长篇来看待,刚开始写的时候没想到要写一个长篇。 写完《红高粱》这个中篇之后,接下来的约稿就很多,我也就觉得余兴未尽还似乎可以接着写。
《高粱酒》、《高粱殡》、《狗道》、《奇死》,就是在1985年、1986年这两年一鼓作气写的。这5部中篇是可以独立成篇的,但它们之间又有联系,人物是连贯的。而且很多情节是交叉写的,时空打得很乱,画面切割得很碎。
因为小说的叙事主人公实际上是“我”。小说还有一个视角,就是“我奶奶、我爷爷、我父亲”这样一个复合的视角。为什么要采用这么一个视角?我想,这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。
我觉得,如果我用第一人称来写战争场面,把我变成了八路军的一个战士,或者变成了小说的主人公,那我觉得很难进入。因为我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,如果用“他”或者用“你”来写,又感觉到一种全职视角写出来有隔膜。
如果我用了“我奶奶”,那么我想,就把历史上的人物,把我的祖先跟我自己紧密地捆绑在一起,我,可以用一个现代的人跳出小说之外来评判小说人物,我还可以以一个后代儿孙的身份来评判我的奶奶、我的爷爷,我也可以跟他们融为一体,代替我的爷爷、我的奶奶的思想来感受小说描写的战斗环境,来感受他们受了伤以后身上所感受的那种痛苦。
他们的饥饿、他们的喜怒哀乐,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变化,这样一种视角,跳进跳出,获得了巨大的自由。
有一年我去东北看“二人转”,突然感觉二人转这种形式就是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。
就跟《红高粱》的结构模式都很像,就两个人在台上,两个人一会儿进入了唐朝,一个扮演李世民,一个扮演程咬金,两个人对唱。突然又进入当下的场景,他们两个是一对搭档或者是一对夫妻在互相调侃,互相给对方进行各种各样的无伤大雅的侮辱。
像相声演员一样。台上的二人转演员突然跟台下的某一个观众开起了玩笑。
“这位大哥,昨天带着嫂子来怎么今天没有带来?怎么昨天带了一个嫂子今天又带来另外一个嫂子。”
是吧?台下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进行了一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。一转眼突然又回到了台上去了。
我想,二人转的演员在小小的舞台上,两个人不断地跳进、跳出,构成了三个叙事空间:一个是舞台进行时的他们,两个演员之间的交流;一个是他们作为一个演员和台下观众的交流;一个是他们所进入了他们所演唱的历史故事当中,这种历史的、他们所扮演的人物与其交流,实际上有三个叙事的层面。
所以说,我们可以完全把它借鉴过来作为小说结构方式。《红高粱》无疑跟二人转叙事的模式有了一定程度的重合。
那么这样的一种结构,实际上给作家的写作带来了非常大的自由。
你没有必要写完全有距离的历史的真实,你可以在小说里,甚至有很多的不确定性。如果你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写一部历史小说,你必须要装成煞有介事的样子来写,你要讲求真实、讲求事件的准确。
如果用这种“我奶奶、我爷爷”的叙事方式,就可以把很多的不确定性,在小说里表现出来。就说我奶奶到底死了没有,在当时到底是中了一发子弹还是两发子弹,她在受了伤以后马上就去世了还是两天后才去世的?这个我不知道。
我在小说里直接这么说。我只是听谁谁说他怎么样、怎么样。可以换一个说法来说,我后来又听另外一个人说,不是那样是另外一种情况。
那么,作家写作的时候完全是天马行空的。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完全是穿插自如的。
我们现在不是讲究穿越吗?我想《红高粱》实际上也是一种穿越。历史和现在甚至我所描写的这场战斗。这个历史事件,前世就是奶奶在牺牲的那一瞬间,忽然想到了她自己的青年时期跟爷爷的一场恋爱或者一场幽会,等于把历史又往前推进了一步,非常的自由。
《红高粱》这部小说,实际上就是一部自由的小说,它所以获得这样的自由,就在于小说叙事的视角的开放性。就是有一个“我”作为叙事者,加上“我奶奶、我爷爷”这样的人称叙事,后来我把五部中篇合成了一部长篇叫《红高粱家族》来出版,所以,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写完《红高粱家族》之后,紧接着我写了第二部长篇《天堂蒜薹之歌》。
3 很多小说的结构都是“二人转”模式

在上世纪80年代,除了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、像略萨的《绿房子》也深受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的追捧。写长篇有一个好故事、有了很多好人物,但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恰当的结构,这也是不完整的。像《红高粱》,实际上是一种拼合式的结构、组合式的结构,它是无数的画面打碎然后穿插、拼凑在一起的。
《天堂蒜薹之歌》也是用了一种三重叙事的结构。
第一重开篇的时候,有一个盲人所演唱的歌谣,盲人用他的歌谣把整个“蒜薹事件”从头到尾唱了一遍。小说主体部分就是作家对事件的、故事的讲述。到了小说的结尾,我把报纸上报道这一事件的长篇通讯,特约评论员文章、社论,作为最后一部分也附上了。这样,就把故事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一遍。
很多小说的结构,现在我看都是二人转的模式。就是历史上的人物的对话、演员之间的对话、演员跟台下观众的对话。
我们写小说的时候,也就是小说里的人物对话、作家和历史人物的对话、作家和读者的对话。这样一种结构,实际上对初学写作者很有用处,可以写得很随便、很自由。
后来,写完了《天堂蒜薹之歌》,大概就到了1987年的年底了,那时候写得非常快,一个月基本就可以写一个长篇小说。本来,写完《红高粱家族》之后,我是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。想写一个长篇系列的家族小说。
《红高粱家族》写的是“爷爷、奶奶”这一代,接下来就写“父亲、母亲”这一代,再接下来就写我们这一代。当时的创作提纲都写好了,但由于生活中不断发生的事件,挤进了我的写作里来,就把那个计划搁置了,到现在也没有完成。
上世纪80年代,就是这么一个探索的热潮。每个作家在写的时候,千方百计,不仅仅在写什么上要突破,更重要的还重视怎么写。包括马原他们,实际上在怎样写上进行了很多的实验。
所以,我们的“先锋小说”,所探索的也不是写什么的问题(当然也有写什么的问题),主要还是怎么写的问题。
我记得史铁生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。他说“像马原他们写的小说,就像一个酒厂里生产的酒一样。很多现实主义作家酒瓶永远不变化,永远是那么一个瓶子,但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酒装到里面去。今天35度的、明天62度的,今天是清香型,明天可能是酱香型的。而先锋小说家呢,酒永远不变,永远都是一种酒,但是酒瓶子不断地变化。”
所以我想,这就是写什么和怎么样写的问题。这是史铁生很形象的比喻。所以,当酒瓶子本身变得很有艺术价值的时候,先锋小说的内容变得并不特别重要,它的形式变得非常重要。
4 常被灌醉写出《酒国》

《红高粱》出版了、电影也拍了,有点名气了。我家乡的一些官员们天天拉着我灌酒,他们每次只要把我灌醉了,大家都非常得意。哪一天没把我灌醉,大家都很痛苦。
所以我每次回去,去的时候是走的,回来的时候基本都是被背着抬着回来的。后来再去的时候,我老婆就说“你不要把他灌醉了。”
但是接我去的人说“放心放心,保证灌不醉。”结果每次都醉。有时快的时候,半个小时就抬回来了。
在高密一年多的破坏性实验,让我对酒文化、对酒场和官场有了非常深刻的体验和认识,还有醉得最厉害的一次。本来已经喝得差不多了,又把我拉到酒厂里去,酒厂厂长说“刚刚烧出好酒来。”然后接了半瓢让我喝下去,三天没醒。
我看了一个人写的一篇文章很有感触,就结合我自己在高密频繁醉酒的经验,结合了这帮人在酒场上,明着是劝酒暗中在进行勾心斗角这么一种体会,写成了《酒国》这部小说。
这是1989年的时候,1989年的7月份,我记得,我和余华住在一个房间里,余华天天往外跑,我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,就跪在椅子上写《酒国》。这样一部小说怎么写?肯定不可能用一本正经的现实主义笔法来写,只能用荒诞的笔调来写。
刚开始用了侦探小说的方式去记录,写一个检察院的高级侦查员奉命到某矿山去破案。据举报矿山干部用婴儿做菜,搞了一个“婴儿宴”。他在去矿山的过程中,就中了美人计。
他本来是要去调查吃人案件,结果自己一到矿山,第一场宴席就被请到“婴儿宴”上去了,当他看着那个“婴儿”端上来的时候,他掏出枪来要去枪毙那些贪官的时候,人家告诉他“把枪放下,这不是婴儿,这是一道菜,头是南瓜做的,胳膊腿是藕做的,眼睛是葡萄做的。”
看起来是婴儿状的一道菜,实际上全都是很一般的食物。这个人,第一场就开始醉,一直到最后他就没有醒过。本来他来破案,结果最后变成了一个被追赶、被追捕的罪犯,最后醉死了。
这时,作家写侦查员破案的小说,在书中,同时收到了一个业余作者的习作。他自称是酿酒的博士。博士不断地跟“我”通信、跟作家通信,不断地把他写的小说寄过来。
最后,我写的侦查员破案的小说,跟业余作者创作的小说融为一体,变成一个故事。作家后来也到了《酒国》,跟侦查员的命运差不多,也是一到那个地方就醉掉了,再也没有醒过来。
这么一种结构的小说,里面有书信,有小说,有作家讲的小说、有业余作者的小说,小说之间本来是虚构的,最后都变成了真实。作家莫言作为一个人物,在《酒国》里第一次出现。
5 《丰乳肥臀》借鉴了颐和园的结构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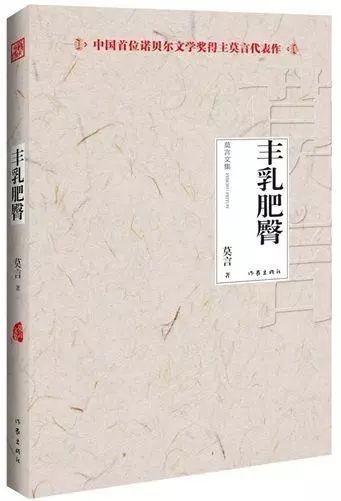
《酒国》写完之后写的就是《丰乳肥臀》,这部小说是1994年开始写的,写的时间确实很短,写了83天就把初稿的45万字写完了,躲到高密故乡的小院子里,没有任何干扰,当时之所以想写这本书,也是因为我母亲的去世。
我母亲一辈子生养过8个孩子,但是4个夭折了,活下来我们4个。我母亲这一代女人都是小脚的妇女,都是很小时结婚,16岁结婚,然后不断地生育。结婚之后上有公婆、下有孩子、左右有妯娌。
在这样一个封建家庭里面,当时的妇女所受的苦难是现在的妇女难以想象的。不仅仅缠脚这种肉体上的折磨。肉体上的折磨最后变成了她们的一种骄傲。
她们经常以自己的脚小作为一种资本炫耀。共产党来了给她们放脚的时候,她们自己要躲到地窖里去逃避放脚。我想像她在封建家庭里,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封建礼教的压制和束缚。
如果一个妇女到了这个家不能生孩子,她是没有地位的。能生孩子,如果一直生女孩,没有生出儿子来也是没有地位的。不单公婆厌烦,丈夫慢慢也会不理你。
实际上,现在回头看,都是非常非常残酷的。就是说,我小说里面所描写的这样一个母亲,是以我母亲这一代人作为一种参照来描写的。
这个母亲,当然跟传统小说的母亲是大不一样的,她很难说是一个伟大的母亲。按照传统的标准来说,伟大的母亲肯定是没有道德瑕疵的,我小说的这个“母亲”,她生的9个孩子是来自于7个男人的。因为她的丈夫是没有生育能力的。
开始,以为她没有生育能力,在这个家庭受尽了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,造成了各种各样的歧视和毒打。最后逼着她只好借种,借种的话一直生女孩,最后终于生了一个男孩。这样一个母亲,当时有文章批判她,说写了一个荡妇,等等。
这篇小说,实际上,也是《红高粱家族》历史家族小说的一种延续。
我刚才讲了,本来计划写两部的,最后在《丰乳肥臀》里把原来很多详细的素材都写进去了。
首先我想,这是一种地方志式的写作。写了高密东北乡百年的历史变迁,这里当初是一片无人开垦的荒地,后来来了四方逃难的灾民、逃官司的罪犯,等等,在这个地方慢慢地定居,几个村落慢慢地扩大,成为几十个村落。一直写到了90年代初,一个荒凉的地方,从一个村庄逐渐的城市化,最后变成比较现代化的中等城市。
这是一个地方百年变迁和发展的历史。作品也另外写了一个家族,以“母亲”为核心的家族,在近百年当中的历史命运,主要写母亲自己所生养的9个孩子的命运。
这9个孩子有的是嫁给了八路军游击队的爆炸大队、有的嫁给了伪军、有的嫁给了土匪,她的八个女儿的命运都不一样。
作为母亲面对着她依附了不同阶层的女儿和女婿们,刚开始她也是很抗拒,但是她的女儿陆续地把自己生养的孩子送回来的时候,母亲伟大的母性就焕发出来了。不管你这个孩子是跟什么人生的,哪怕你跟伪军生的,你送到我家里来也是我的后代,他也是一个生命,我也要把他养大。
我这个小说里,自己感觉到比较特殊的一点,还是写了上官金童这么一个男性的形象。在批判这部作品的时候也是饱受诟病的。
因为上官金童是母亲生养的9个孩子里唯一的男孩,从小就在姐姐们的呵护之下,母亲为了让她的儿子长得健康,就不断地延长给他喂奶的时间,以至于当他到了上小学的时候,每天上午母亲还要到学校的门口给这个儿子去喂奶,正是因为他不断地吃母乳,他拒绝吃食物,到了他30多岁的时候,还是不能像正常的人一样生活,所以,包括他母亲,最后也非常反感痛恨他不成材。
就说“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站着撒尿的男人而不希望生养像你这样一个,一辈子吊在女人乳房上的一个窝囊废。”
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,是一个象征性的细节,在农村里面,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吃奶吃到七八岁的孩子,但是像这样一个到20多岁、30多岁还不能吃别的食物的人是没有的。
我觉得这个人实际上就是一种象征。
我在长篇的结构上一直还是比较硬性的,像写《丰乳肥臀》40多万字的这样的一种历史家族小说结构也是必须考虑的。我们当然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按照编年史的方式,一年一年往后写,但是这样读起来势必觉得很沉闷。
我就想到了颐和园的结构,颐和园一进门旁边有一个“园中之园”,园中之园是颐和园的一个组成部分,但是它同时也是别有洞天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园子存在的,所以在长篇《丰乳肥臀》里面,开篇实际上我是写的一场战争,这个家庭正在生最后一胎孩子,就母亲在生她的双胞胎最后一胎,同时他们家的毛驴是在磨坊里面难产,母亲生双胞胎也在难产,那么在河堤上这时候游击队正在设埋伏,正要突击日本人的汽车队。
那么这样三个场面交叉着描写,而这个家庭里的这种家长,像母亲的婆婆和她的丈夫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