忽如一夜诗风来。
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,在这几年,诗歌似乎开始呈现出重回C位的隐隐势头。有人穿越大半个中国,只为倾倒孤注一掷的狂热(余秀华);有人从空气里赶出风,从风里赶出刀子,从骨头里赶出火,从火里赶出水(王计兵)。职业诗人笔耕不辍,专家学者也灵光乍现,赋诗自乐。美术馆、书友会传来朗诵诗歌的声音,各类微信公号、App推文亦经常发送“睡前小诗”一首,追慕雅人深致的风度。明星、要人们读诗,普通百姓们同样读诗——虽然,这一轮滚滚诗潮目前看来,远未覆盖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光芒,但的确已经足够闪烁,构成话题。
子曰:“小子何莫学夫诗!诗,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: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,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不拘形式和体裁,充满魅力的诗歌,探讨爱情、社会、艺术、人生、哲学……每一行文字的吐纳,回应着一颗心脏的悸动,宛然拨开喧哗鼎沸到抵那个鸿蒙初辟的原点,宛然一梦。
飞光煎人寿,幸好我们还有诗歌,不管天高地厚。
中途诗事
老早的年岁见过璀璨的星群视作日常
此后所有的夜空 都会被它们的前身
暗自增添深邃的可能
汨罗江畔,芙蓉雅集。今年5月20日,第一届“芙蓉文学双年榜·芙蓉文学图书榜”入选作品揭晓,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的《三行集》,成了此次唯一入选的诗集。该书一页只印三行字,有大量留白处理,充分释放字、词、句本身的能量,使之自由自在。上榜辞称:“心开意适,三行成诗,记述细微的人事,倾听微弱的声音,即便是关于词语、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深沉思索,也低语徘徊、轻声争辩。凝视生活的瞬间,辨析内心的响动,张新颖以他的敏锐、体恤、想象和思力,发现渺小事物的光泽,也守护了语言的尊严。”
但时间倒退回198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:大一新生小张走进学生活动中心的一个房间,人已经聚集了很多,灯光忽然一暗,又忽然大亮,复旦诗社的活动正式开始。诗,关于诗的理念,主张,辩论……灯光下那些年轻的脸,泛着特别的光芒,激动的情绪混合着不羁的才华,满屋子横冲直撞。“我好像是要躲避这些才华和热情,活动还在高潮迭起,就悄悄退了出去。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,我认定自己不是做诗人的料。沮丧吗?多少有点,但远远谈不上严重。那个年纪,会以为人生的可能性选项多到数不过来,这只不过是在纸上划掉其中的一项而已。”
诗歌风行的年代,校园里弥漫着特有的兴奋和抒情气氛,张新颖置身其中,却仿佛又绕开了。他不写诗。更准确一点说,偶尔写,写得不好,也不怎么当回事。例外的是,用心做了一个“实验”:写了一组“读书笔记”,形式却是诗。
这种含混的写作从1988年持续到1995年,可见兴致和轻微的沉迷。张新颖以为,随着青春时代的结束,此般“自娱”大概会渐渐消失。不料,40多岁的时候,2011年,忽然又写出一组《“剪辑”成诗:沈从文的这些时刻》来——“我要把这些时刻从时间的慢慢洪流中挑出来,我要让这些时刻从经验的纷繁芜杂中跳出来,诗是一种形式,更是一种力量。”“写这组诗当然与我的沈从文研究有关,但私心里,并不情愿把它看成研究的‘副产品’。”
教书的头两年,张新颖编选了一本《中国新诗:1916—2000》(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),20年了,这本书还在印行。“当时做这个工作,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上课的学生方便,我开了一门‘中国新诗’的课嘛。每次面对新一级的学生,我总是这样开口:你选这个课,要想想它和你有什么关系。特别是,如果你不写诗,将来也不做新诗研究——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吧,你和它可能形成什么关系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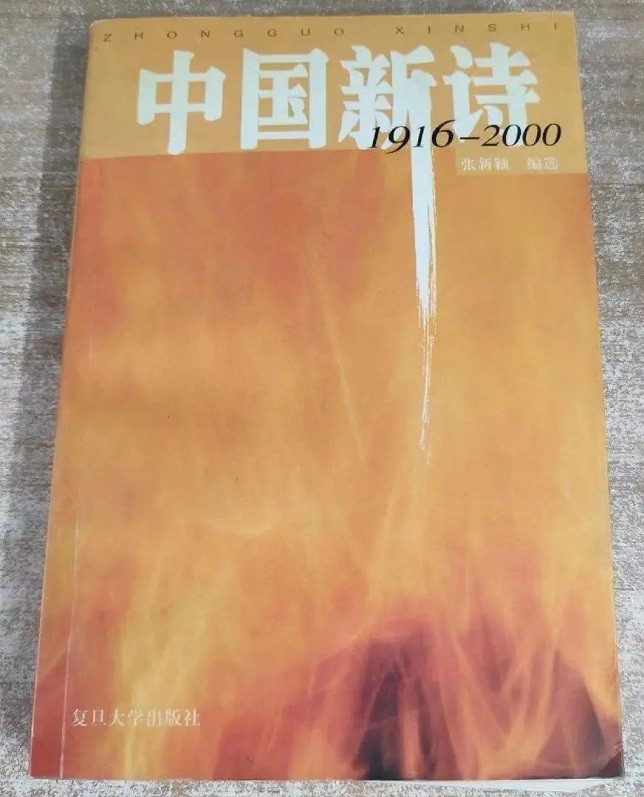
这样说了十年之后,张新颖发现,自己不能再用“如果你不写诗”作开场了。2011年的某天,他在办公室写毛笔字,裁纸时不慎碰倒了杯子。看着用了多年的杯子从桌上滚下,碎了一地,刹那工夫,张新颖“心理上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”:“紧张地盯着它,仿佛要用眼神阻止它跌落;等到碎裂的声音响起,倒是松了一口气。我把这个心理过程用毛笔写下来;又想,杯子是个器皿,盛水或牛奶或酒,也有别样的‘杯子’,盛的是事业、感情、身份或者其他种种,这样的器皿,也可能会碰倒、碎裂。那么,我顺手涂出来的句子,似乎多少有点意思。就又在电脑上重写一遍,短短地,叫它《杯子》。”
之后,在各种各样事务的间隙,不那么经常地,会有什么感受和想法,促使张新颖拿起手边的铅笔、钢笔或水笔,在眼前的一张纸或一个本子上记下来,等待其完整成形。他放松地写平常的经验,平凡的呼吸,写中年自甘平庸的诗。2017年,诗集《在词语中间》出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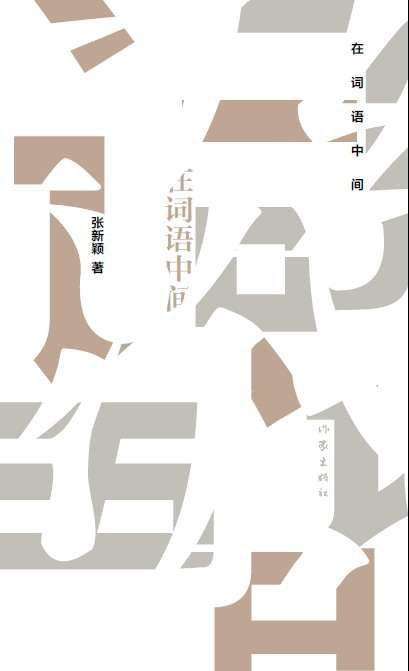
2020年,《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》出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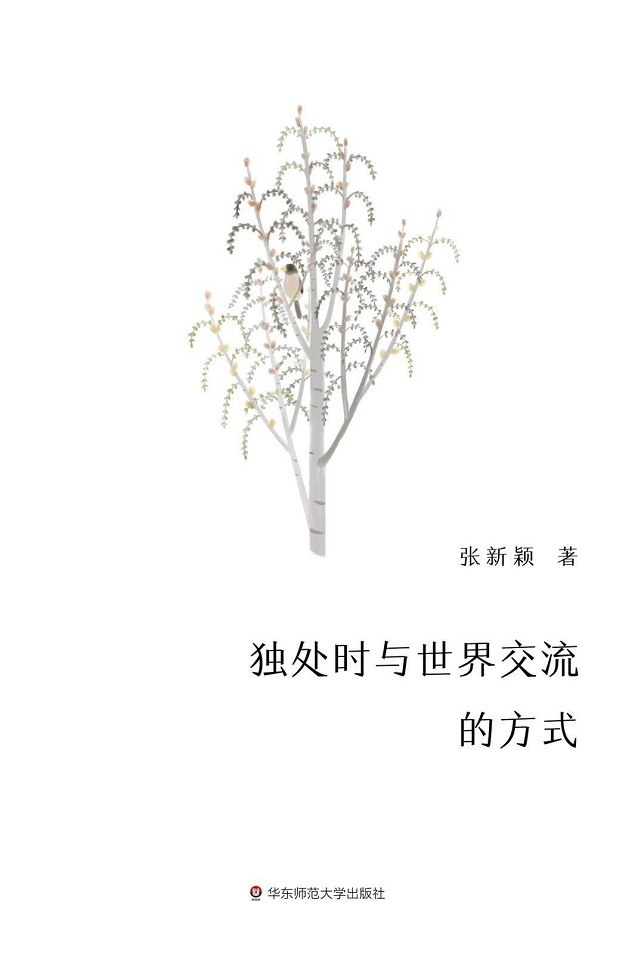
2021年,《三行集》出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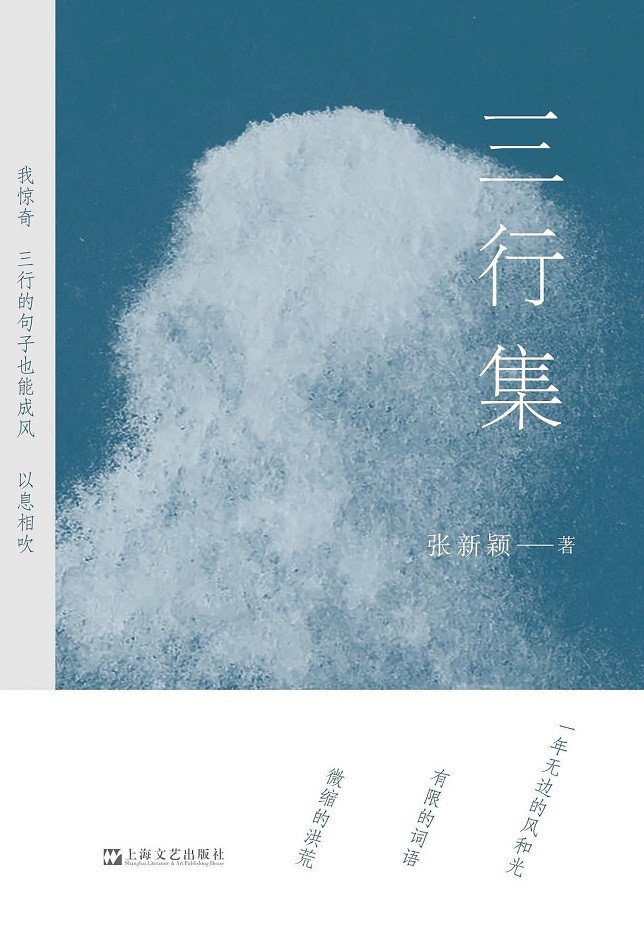
但张老师仍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。“表面一点说,我不想要诗人的习气;根本上,我不想要诗人的限制。我要随意、自由一点。”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记者采访时,他亦强调:“我实际上不是诗人……很难说我写诗具体是从哪里入手,不过最终的‘成品’,表现的好像都是日常的生活,是一些‘细枝末节’,碎屑的感觉和想法。我对自己没有限定、没有要求,就是当突然有个东西、有个时刻击中了我,不管这件事是大是小,是现实是虚幻,我可能就被触动,从而写出一首诗来。所以,于我而言,一首诗的诞生是没法计划的,有就有了,没有就没有。我也不会产生‘写不出’的焦虑,顺其自然,随遇而安罢。”
身边写诗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?张新颖的回答是,上世纪80年代以来,一直都有写的人,不少;